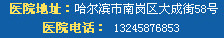常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最喜欢村子上有人家过事情了,或者是喜事、或者是丧事,或者是其他重要的节日,一方面是热闹,由于那时的农村娱乐和消遣的方式比较匮乏,所以一到这时,就莫名地兴奋,另一方面就是特别喜欢那时候的扩音喇叭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将一个非常大的扩音喇叭高高地放在树杈上,然后播放一出根本就听不懂、听不清的秦腔来,老远老远的邻村都能听见声音,不知道有多神气、多热闹了。
后来走出大山,到外面上了学校,陌生的人多了,来自四面八方,感觉莫名地孤单和失落,好在同宿舍住进了一位基本上算是老乡的同学,这给自己不少的慰藉,一起住的久了,才发现,这位同学竟然是一位秦腔迷,成天捧着个随身听在不厌其烦地播放秦腔磁带,耳濡目染就渐渐地喜欢上秦腔了,并且学会了哼唧几句,然而也不过是觉得熟悉、有老家的味道罢了。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生活阅历、人生经历的丰富和老成,年少时的轻狂和贪玩逐渐退去了不少,忽然发觉自己可以娱乐、聊以解闷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而且有个不好的脾气就是对外面的各色各样的娱乐比如看电影啊、打游戏啊等等地总是提不起兴趣来,日子逐渐苦闷起来,一天除了写点东西之外好像就无所事事了,电视也不爱看。
忽然有一天,想起了秦腔来,并且一时间兴味大增,把个齐晓春的《下河东》翻来覆去听了无数遍,爱人在傍边抱怨我老了,像个老头一样,我莞尔一笑,不过话又说回来,喜爱听秦腔或者学唱秦腔的人,大多都年龄偏大,这是事实,以前的时候听听秦腔觉得稀奇好玩,觉得听见声音就满足了,现在听秦腔却在逐字逐句地记,逐音逐调得感受,才发现,秦腔里面的世界,精彩无限,回味无穷。
以前在农村,水远山高地,人们在原野里一面汗流浃背的劳作一面扯开嗓子毫无顾忌地吼一段秦腔,怕是有使不完的劲了,并且完全可以把自己压抑于心的苦闷通过吼得十分难听的秦腔给释放出来,或者把自己心中埋藏很久的想法通过秦腔给喊出来,我总觉得这种肆意的发泄给人带来的轻松远远超过了秦腔本人给人带来的惬意来。
现在来到了城市,狭小的居住空间根本不容许人们肆意地吼唱,于是,秦腔也就渐渐地从城里人的记忆和生活中走远了,人们也渐渐地适应了秦腔的缺失,就连专门的戏园子也很少有人光顾了,人们发泄放松的渠道减少了,所以生活的压力渐增,城里人精致、乡里人随和,城里人匆忙、乡里人散漫,城里人计算,乡里人大方,这也大概就是有些城里的人们羡慕乡里的人们的一个方面吧。
秦腔逐渐听的多了,就喜欢琢磨起秦腔里面的喜怒哀乐来,峰子记得最清楚、最深刻的就是孙存碟的秦腔丑角戏《拾黄金》,里面把一个好吃懒做、不务正业而导致家破人亡、一贫如洗的乞丐胡来演绎地活灵活现,而且精彩的唱词也耐人寻味,比如悔恨自己的所作所为给自己带来乞讨这般下场后的一段唱词,“想起了二爹娘我好不心酸,提起来讨饭事我好不羞惭,倒不如做农民自耕自穿,倒不如铁匠铺去铲煤碳,倒不如学唱戏快乐无边,倒不如学卖挡胡谝闲传,倒不如学耍猴去钻圈圈,此间莫把苍天怨,只怨我懒病把身缠,”,多么好的唱词啊,其中的韵味令人回味,催人泪下。
作为一个西北人,峰子自然对秦腔这种戏曲的喜爱程度是无以复加的,总觉得这不仅仅是出于好听或者消遣而喜欢的,感觉秦腔的这种豪迈、这种尽情、这种味道、这种震撼历久弥新并且刻骨铭心。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l/2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