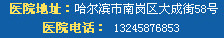联合策划|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促进中心、能镜
前言
上燃动力的20年,是一个时代、群英与个体共同塑造的故事。
如果将其视为时代变迁所导演的一幕年代剧,它的丰富性和典型性足以问鼎国剧之巅。
官、产、学、研,与其命运关联、轮番登场的不同角色,在高高低低跌宕起伏的剧情里,在中国燃料电池事业发展的曲线里,理想曾经翻涌沸腾,荣誉曾经缀满枝头;转瞬而来的行业低谷里,迷雾笼罩、前途未卜,出走、坚守、支撑与拯救的关键元素,也一个都不曾缺少。
年,历经曲折、几经颠沛,被一批坚守者奋力保护的上燃火种,被在氢能领域悄然布局的长城汽车重新点燃。
先天为零、却怀坚定战略的长城氢能团队,与先天具足、独差一次机会的上燃动力,在氢能产业开始回春的这一年,如同卯榫相合,融为一体。某种程度上,这次相遇,是一种必然。
年12月14日,上燃动力成立20周年,在长城体系「充血」3年的上燃动力,一口气用4个发布来宣布其真正的重生。
kW大功率燃料电池发动机;中国首款获第三方权威认证的70MPa减压阀;与荣程钢铁集团,一起打响钢铁企业绿色运输减碳攻坚战;与房地产热电联供、氢能船舶、多城市物流和卡车场景等领域签署战略合作,推动氢能社会多场景的赛道布局。
这并非只是上燃动力的重生,也是在起伏跌宕中飘摇20年的中国氢能产业,第一次稳稳地站在了新能源世界的入口。
上燃动力20年,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促进中心和能镜寻访其间的关键个体,推出,分别从政府、科研、整车厂、关键零部件以及新起点等不同视角,讲述上燃动力令人无法忽视的往事。
这段历史不仅属于上海和上燃动力,更是中国氢能产业20年的一个缩影,一扇窗户,每一个在起伏和幽暗中坚持的氢能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看到身边的同行人。
今天的讲述者,是长城未势能源总裁陈雪松,作为氢燃料电池领域浸润20年的技术专家、坚定的自主之路的践行者,他的职业命运与高光时刻,先后与上汽和长城相连,而这两家公司,一家国企、一家民企,一个氢燃料电池整车领域的先行者,一个氢能产业链拓展的后起之秀,皆因上燃动力,有了共同的交集。
透过陈雪松的讲述,可以看见长城汽车发展氢能战略里,有两条线索在交织。一条锁定氢能前途和方向,另一条深嵌对自主人才和自主技术的渴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拯救者的角色最终是长城,而且,似乎,也必然是长城。
以下是陈雪松的口述整理
现在回忆起来,我加盟长城未势,就好像一场酝酿已久的缘分——之前所有的积累,注定要在这里,获得一次彻底的绽放。
那是年10月,长城已经在氢能之路上探索了三四年,那支后来被解密的「秘密部队」里,国外专家云集;而头一年,曾经缀满辉煌历史又被现实拖拽至低谷的上燃动力,也被长城收至麾下。
这家著名的民营汽车制造商,的确打算在氢能领域真刀真枪地干下去。现在,它的手上握着诸多棋子,正在谨慎思考该如何出招,下出一盘好棋。
我,一个刚刚从加拿大归来,又曾在上汽历经8年「抗战」,推动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的行业老兵,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赋予了一种责任和使命,出现在这家公司承前启后的历史交叉点上,得以承接一段历史,并继续参与一段新历史的书写。
从煤到氢
整个故事,还是先从个人经历说起吧。
算起来,我在氢燃料电池技术研发领域摸爬滚打,已经超过了20年,但最初,我是研究传统能源起家的。
文革后,大学恢复高考。年,17岁的我考上辽宁科技大学,成为老三届中的一员,求学和职业生涯,从此和能源二字密不可分。
本科毕业后,到煤炭工业部下属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继续念研究生,师从王兆熊,研究煤碳清洁利用,主要方向是研究煤变气,煤变油。当时国家出于能源安全考虑,要在这一领域提前做储备。
硕士毕业后,我还研究过一段时间活性炭,用煤制造多空吸附颗粒用于净化水。年北京亚运会所有饮用水能够达到国外标准,得益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和突破。
年,我拿到一笔奖学金,得到去英国读博士的机会,研究方向是高强度轻量化合金材料。就这样,在正式踏入氢燃料电池大门之前,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研究方向几经转换,尚无定向,直到年的到来。
年,我博士毕业,经同学介绍,移民至加拿大。第二年,作为第9号员工,加盟当时还是间小公司的Hydrogenics(水吉能),开始介入开发和制造水电解制氢和氢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和产品,从此一脚踏入氢能门,遂成毕生的研究方向。
当时Hydrogenics条件非常简陋,办公室在一栋小两层的房子里,夏天没空调,大家大汗淋漓,给通用汽车实验室的合作项目制造燃料电池电堆测试设备。
机子造出来,发现太大,既下不了楼,也没办法从窗子里送出去,大家索性在墙上凿出个大洞当通道。那些从无到有的日子,虽然艰难,但每天都在学习和创造,回想起来也蛮有意思。
后来Hydrogenics不断壮大、上市,年又被康明斯收购,这已是后话。得益于那段经历,我在其中一路成长,成为公司重要的技术专家。
从上汽到长城
年,我得到一个重要机会,决定从加拿大回国,加入上汽。
那时,我已是Hydrogenics的重要技术骨干,从科学家一路做到部门总监,当年公司上市必备的三个专利中,其中一个就是我贡献的。
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加拿大的旖旎风光和舒畅的生活工作环境,惬意又舒服。但回国干一番事业的想法可能一直埋在心里,它在看似平静的湖面下蠢蠢欲动,直到被好朋友黄晨东点燃,并熊熊燃烧起来。
黄晨东早些年在北美福特工作,负责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开发,经常到我们实验室做实验。我俩都是华裔,研究方向又相近,遂成为好友。
8年,他先回国,以海外专家身份加入上汽,任新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黄晨东希望我能回国和他一起推动产业发展,他说服了我。
当时,上汽还是上燃动力大股东,走在国内整车企业研发氢燃料电池最前沿,得益于8年奥运会和年世博会的拉动,国内掀起了一波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小高潮。
年11月1日,从加拿大回到上海,跟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干频及团队见了面,10天后,也就是「光棍节」那一天,我正式加入上汽,担任上汽氢燃料电池前瞻开发团队的总监。
此后8年催生了上汽第三代氢燃料电池技术,在电堆功率等多项核心技术指标上的一路领先,并实现了主要一级零部件自有国产化。
上汽在整车厂研发氢燃料电池汽车的领域一路绝尘,并在年成立上海捷氢,以加快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发展。
年,我已经58岁。高强度的工作,加上年岁日增,身体出了些问题,遂向上汽提出离职,准备回加拿大修养身体。上汽领导诚心挽留,大家觉得可惜,但客观情况摆在那里,最终还是回到了加拿大。
休养调整半年后,身体渐渐恢复。之前的同事希望我能再回Hydrogenics。但年,康明斯拓展氢能战略,收购了水吉能,公司管理架构改变,也便就此作罢。
这时,长城缘分的枝蔓开始生长并伸展了过来。
年,长城确定氢能战略方向,在内部组建了一支「秘密团队」,开始探索氢能领域的发展,他们招聘了宝马氢能团队负责人Dr.TobiasBrunner来主掌技术和研发,并从国际和国内氢能大公司招来大批行业专家和技术带头人。
年10月经朋友推荐,我跟长城集团董事长魏建军董事长见了面,感佩于他对氢能发展大势的敏锐,也强烈感受到长城要在氢能领域拓展的决心,当时,他们已经在技术研发领域投入了几亿元的巨资。
这是一家不惜血本也要把事情干到最好的公司,这一点已经融在长城的基因里,在它过去所创造的多个「第一」中,一次次证明了这种力量的强大。
我被魏董事长高瞻远瞩的氢能战略和做氢能的决心所感染,决定加入长城,主管氢能业务。
从两个团队到一个集体
年4月,长城整合旗下氢能资源,成立未势能源,开启独立市场化运营的道路。6个月后,我正式加盟未势任总裁,与董事长张天羽配合,主管技术与研发。
上一年7月,长城已经完成了对上燃动力的全资控股,这家浓缩了中国氢燃料电池发展史、缀满沉甸甸的荣誉和技术积累,又历经坎坷的公司,成了长城大家族中的一员。
长城当年的收购行动,既是纾困之举,又是战略行动——解决了上燃动力当时的资金困境,接掌了一系列的技术储备,又在人才聚集和氢能发展最繁茂的长三角地区,建立了一个根据地。
此时的上燃动力,一直在行业低潮中坚守,虽然火种尚在,但团队几经离散,只剩下几十人。
长城入主上燃动力之后,开始思考如何为之定位,又如何重新激发它的活力。
当时,保定团队是基于乘用车开发氢燃料电池系统,尚无商用车布局,所以便定下彼此的分工——上海保定两个团队,前者负责商用车燃料电池系统开发,后者则专注乘用车。在外部竞争不足的情况下,大家还可以通过内部赛马,提升产品和技术的性能。
但显然,已经支离破碎的上燃动力团队需要重建。我重新召集起已经离开上汽、各求发展的一班旧部,组成一支十多人的系统集成骨干团队,很快就把商用车发动机做了出来,算起来,这也是国内最早、最大功率上公告的产品。
就这样,两个团队并行,向前走了一年多。
当年,上燃动力伴随国家「」电动汽车计划启动,在各界领导和行业专家支持下成立,此后在大型赛事和活动的带动下,技术和产品屡屡创新,对于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细看历史,无论8年北京奥运会,还是年上海世博会,大家做的都是项目,而非真正的商业化量产,因此也一直未能达到整车厂规模化生产的水平。
上燃动力缺乏体系化思维和对商业化产品的理解,而这,恰好是长城体系所具备的优势——长城有正规的零部件开发体系、系统集成体系、软件控制体系等等,它的标准、流程、验证、设计、评估都很完备。
体系的赋能慢慢在上燃动力开始体现,而两个团队在经历了并购初期的磨合后,也开始走向统一。
从年到年,我们用了差不多一年的磨合期,将乘用车和商用车两个团队整合成了一个集体。未势、上燃,从团队构架上,真正成为了一家。
从依靠外国专家到自主研发
我到未势来,其实还担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建立长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正向开发体系。
起初,长城氢能发展战略,是以国外专家为主的,当时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技术人才,的确在长城氢能体系从无到有的构建中,起过重要作用。
但随着时间推移和未势发展需要,一个问题开始摆在所有人面前——对国外专家和他们过往经验的过度依赖,导致一些项目虽然花费颇多,但并未提高效率;一些技术项目,价格高昂、流程复杂,却并未有任何结果上的保障。
这种情况,在我加盟未势前,魏总已经有所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l/30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