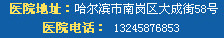伏珠--我可爱的家乡
伏珠煤矿满山沟
文/张三平
自古以来,伏珠的沟沟坎坎里都打出煤窑。小时候去地里挖野菜,经常会发现一些深洞,杂草掩映,大家都叫它们“洞”,读同,与洪洞的“洞”读音相同。这都是些废弃的煤矿。
后头院里杵杵爷家,在北滩里打出软碳窑,发了家,盖了几十孔窑洞的大宅子,受当时不让占耕地死限,不然建一个乔家大院都有可能。
柳沟里有个干碳窑,据说出产的干碳又硬又耐烧。七八十年代,底下滩汽路上下,各打出了一个优质煤矿。路上是伏珠大队矿,叫大队窑,路下是刘家垣公社矿,叫水窑。
两个矿都产优质碳,人们叫高碳,有二尺高。煤矿有技师,叫“老人”,指导如何走巷,每走一截儿,立即用两米左右、碗口粗菜木柱儿顶住。挖煤工用一个鹤嘴斧头掘进,后来用上雷管与炸药。拉煤工最多,一个铁皮平车装上煤,身子几乎躬成九十角,拼命往外拉,遇到上坡路,有专门的半大小子在后面推。巷道黑暗、寂静,水滴与汗水在身上横流。拉到竖井口底,倒进一个铁皮斗子内,井口有个专门开绞车的人,开动机器把一斗煤拉上去。井上一个人用一根长钢筋钩开斗子门,“哗啦”一声,一斗煤漏进斗下平车内,一个专门拉平车的人把煤拉到一个坡顶,“哗——”一声倒在坡下煤场。煤场内,大车、拖拉机、头牯车、平车等等着拉煤。
大队窑出碳后,公社才开始打窑,窑址原先就打过窑,打出水后,当时没有排水技术,无法开采,只能回填。现在有了水泵,水可以排走,公社才开了窑,因经常往外抽水,所以叫水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两座窑像两颗明珠镶嵌在公路上下方,又像两座聚宝盆,流出了滚滚乌金。汽路上车水马龙,工人一张乌脸,一口白牙,佩着矿灯,脸上带着光芒。回家后,家里人让好吃好喝上。坐在一起,聊天内容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月上了多少个班,可以领到多少工资等。
两座窑相隔几十米,为了抢夺资源,都拼命往对方那边掘进,终于有一天,两座窑打通,双方经过协议,各自相安无事。
下煤窑自古以来都是高危行业。在那些年代里,感觉每年伏珠村都有死于矿难的人,甚至一年有两三个。人们说,下煤窑是四块石头夹一块儿肉,很恐怖。一些工人从坑下上来说,唉,今天又见到了一次日头!生死难卜,艰辛异常。但仍然有年轻人为了生活,为了改变命运,前赴后继地去下煤窑。反过来说,那时不去下煤窑又能去干什么呢!
改革开放后,国家允许个人开矿,伏珠人立即行动起来,河垄头、沟沟、鸡蛋葫芦、房子沟、北沙沟、老沟、南凹里、窄井里等,到处是开窑人。这些窑有的出了碳,有的没有出,受资金限制,大多数赔得一塌糊涂,只有极少数人发了财,成为传说中腰缠万贯的窑主。
煤矿的兴旺带动了当地经济的暂时繁荣,机电设备、交通运输、餐饮业等一时兴盛无两。伏珠村由此产生了大量车主,不过几乎都赔了钱。
年前后,国家严厉打击了私挖滥采,整顿了煤碳行业。伏珠的煤矿终于偃旗息鼓。当地的煤矿只保留了霍矿迴坡底一座中型国营矿。不甘心的村里人等了几年,看到政策没有松动迹象,只好纷纷外出打工。
现在,你去伏珠的沟沟壑壑走一走,在耙得平展展的地中,在茂密的杂草中,时不时会看到一个硕大的洞口,你一定不要奇怪,说不定,这个地方当年曾机声隆隆,烟尘飞扬,人欢马叫过。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l/631.html